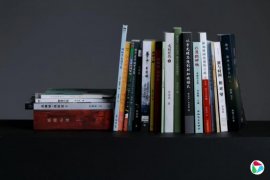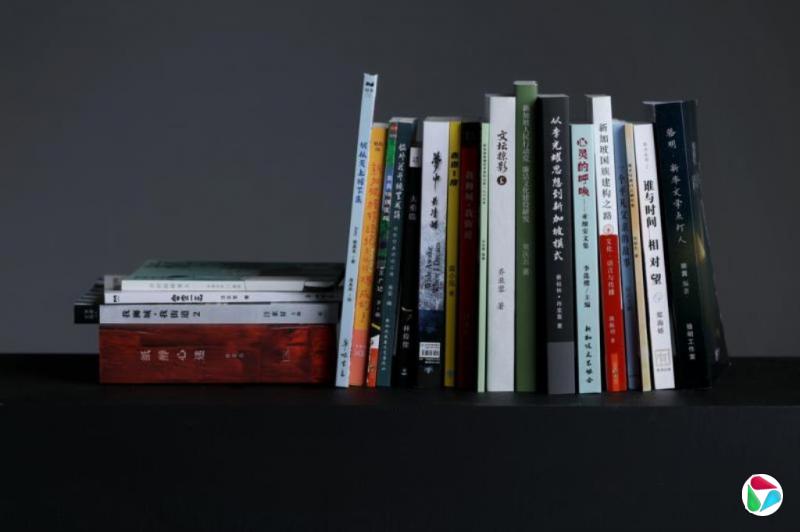
黎紫书又要来新加坡了,这回邀我来一场对谈,我自然深感荣幸。她拟了个题目:此岸与彼岸——两个过河的人。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,正好和我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相关:作为小场域的华文文学,要怎么走出困境?要如何“过河”?自己架桥,乘船,还是能再有什么办法?
除了写作,我也经营一个独立的小出版社:水木作坊,10年来出版了七八十种文集。据我的观察和切身经验,由于阅读习惯变化,加上新加坡人口规模和市场窄小,华文实体书越来越卖不动,上个世纪一种文集还能卖出三五千本,现在只能卖三五百本,甚至一两百本。书本难卖,自然挫伤作家和出版人的创作与出版热情。一些资深作家甚至对结集出版作品都提不起劲,因为书本出版后往往只能堆积家中,送也送不出去!不得已卖给加龙古尼,一公斤只有5分钱!令人唏嘘。
如何打破这个困局,使本地华文写作能够保持应有的热度?我认为,积极“走出国门”是一条重要的出路。以下几种方式值得尝试和推广:
一、到海外出版作品:将作品推向更大的华文读者群。
二、参加国际创作比赛与文学交流活动:提高作品的能见度和影响力。
三、争取条件将作品翻译为外文:这是迈向国际文学舞台的关键一步。
?这些并不是我个人的空想,而是一直有出版社和作家在身体力行,并取得积极成果。例如季风带出版社、作家英培安、尤今、谢裕民、陈志锐、黄凯德、语凡、林韦地等。
以我个人为例,多年来的个人文集超过一半是在国外出版,销量都远超国内,有的还能做到二刷。更难得的是,这带来与国外文化团体和作家的交集,有机会受邀参加国外的文学交流,作品入选海外年度文选和奖项。如果有条件把作品翻译为英文、马来文等外文,能让作品走得更远,这些都是对创作者极大的激励。
去年,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受到全世界瞩目。韩语作为一个小语种,如何被国际社会认识并获得殊荣呢?原来,韩国政府早在1996年便成立韩国文学翻译院,搭架桥梁使韩国文学走向世界。
查阅资料得知,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:翻译资助、出版支持、人才培养、国际交流和海外推广。至今已支持用44种语言,翻译出版超过2100多部韩国文学作品。从韩江的获奖,不难看出除了写作人自己的天赋和努力,国家的支持也非常重要。“韩流”涌动背后有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。
在1980年代,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同属亚洲四小龙。在经济方面,我们至今毫不逊色。可是,在文化生态和软实力的建设上,我们明显有所不及。是不是在国家的支持和投入方面,还有努力空间呢?比如说,我们的作家到国外去出书,是近年来常见的现象,挺不容易。然而,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在采购时,并没有通过更灵活的方式给予支持,仍主要以国际书号(国内)作为采购标准。这种以出版物的书号,而不是以作家国籍作为考量,本国作家在国外的出版物往往被忽略,作家抓到一头,丢了一头,对他们走出国门出版作品,起不到鼓励作用。
在文学交流资助方面,眼下基本上也是由出版社或作家自行筹措。国家虽然通过文化部门(如国家艺术理事会)提供资助,但似乎不够“给力”。例如,当你申请出国交流赞助时,艺理会会问:“对方是否已提供补贴?”如果对方有补贴,似乎就没有申请的必要。这种思路令人费解:难道我们自己的作家,反倒主要由别国来资助?一般来说,对方提供的只是部分活动补助,无法抵消全部开销。艺理会的赞助如能更加慷慨,将能减轻作家的负担。
至于翻译支持,我们或许无法做到像韩国那样成立国家级文学翻译院。但至少,文化机构可以为翻译本国作家的作品提供资助。我的短篇小说集《可口的饥饿》,由本地翻译家程异翻译为英文,却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南方翻译奖学金的赞助下完成。该书在英国出版后,成为首部获得英国笔会奖的新加坡小说集。今年在美国上架,又入围亚洲协会首届夏白芳图书奖。
在选择对作品的赞助与取舍时,秉持更加包容的态度,以文学性为主要标准,是对创作起到积极推动的关键。例如韩江作品《少年来了》,因为涉及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历史创伤,在官方支持上曾面临复杂的考量,但最终得到更广泛的肯定。
当然,以上对国家文化机构提出的意见,并非否定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努力,一些赞助项目是一直都有的。
?对于小语种、小场域的文学而言,“走出国门”需要能力、运气和机缘。希望在民间的努力之外,国家也有具体措施来推动,多想想还有什么可以做的:加大支持力度,简化申请程序,使支助的覆盖面更广、更有效率。
?紫书就要来了,她漂洋过海而来。现在她早已不止“过河”,可以说是“过海”去了!在获得许多国际声誉之后,从她的经验之谈中,相信我们定能受益良多。
作者是本地作家